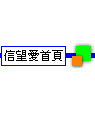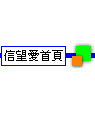火紅的鳳凰花,是我對瓦哈卡(Oaxaca)最深刻的印象。仲夏時分,在地球的另一端,看到沐浴在燦爛陽光中的鳳凰木,不知不覺就回憶起遙遠的,也同樣燦爛的大學時代的日子。在台灣,每當紅花盛放的季節,也是驪歌高奏之時。記得五年前,我曾在校園的紅花下默禱,希望離開校園後,可以在社會上好好的闖一闖。沒想到五年來跌跌撞撞的,會有機會闖到這麼遙遠的國度,像重遇故友那樣,與紅花相會。
火紅的鳳凰花,是我對瓦哈卡(Oaxaca)最深刻的印象。仲夏時分,在地球的另一端,看到沐浴在燦爛陽光中的鳳凰木,不知不覺就回憶起遙遠的,也同樣燦爛的大學時代的日子。在台灣,每當紅花盛放的季節,也是驪歌高奏之時。記得五年前,我曾在校園的紅花下默禱,希望離開校園後,可以在社會上好好的闖一闖。沒想到五年來跌跌撞撞的,會有機會闖到這麼遙遠的國度,像重遇故友那樣,與紅花相會。
回憶超越了時空,我對著紅花拍照的時候,視線穿過鏡頭,又再看到紅花下,一個個穿著黑袍子手拿著四方帽的身影,當中有您也有我。我們的笑容是如此坦率、燦爛,有如天真的小孩。面對未知的前路,我們不能一一攜手同行,但在離開校園之前,都真摰地握手祝福。這些珍貴的情誼一直陪伴著我,我覺得心頭有一股暖流流過,多麼希望與好友們分享這一刻,在異國小鎮的美好時光!
我們從 SC 乘長途巴士往西行,清晨時份到達瓦哈卡。每到達一個新的點,第一個活動都是找旅館。我們在旅遊書上選的那一家租金太貴,為了以後能夠有足夠的旅費走更長的路,我們背著沉重的背包,在附近找其他便宜的住處。
因為太累,也沒有力氣去挑剔了。我們在一間非常簡陋的旅館安頓下來,除了租金便宜之外,這裡別無優點。房間只有一張雙人床、一套學生寫字的桌椅,還有一個衣架之類的東西。唯一的窗戶就在大門旁邊,朝著外面的走道,如果我們打開窗戶的話,所有經過的人都可以對我們的房間一覽無遺,而且可以伸手進來拉開大門的鎖。因此,在炎熱的夏天,我們都必須把門窗全部關緊才能睡覺,沒有悶死實在是奇蹟。
更糟的是,供住客使用的共用衛浴設備都非常的髒,這對於有一點點潔癖的我來說,實在是很難忍受。簡單的梳洗之後,也沒有洗澡、睡覺,我們就離開旅館,趕搭往蒙特阿爾萬(Monte Alban)遺蹟的巴士。趁著當天星期天,參觀遺蹟和博物館免收入場費之利,我們必須爭取時間。
被西班牙人稱為「白山」的蒙特阿爾萬,是我們在墨西哥參觀的最後一個遺蹟。Zapotecs 人選擇了這一帶居高臨下的地勢,築起了佔地約四平方公里,綿延七個山頭,氣勢雄偉的山城首都。我登上中心廣場的金字塔,俯瞰四周的瓦哈卡谷(Oaxaca Valley),覺得天地何其廣闊,人手所造的功業再宏偉,也只不過是叢林中的一角而已。
也許是大家都有點倦意,我們中午就回到瓦哈卡,一方面找一家比較像樣的旅館,另一方面也要好好參觀一下這個種滿鮮花綠樹的小鎮。瓦哈卡在 1486 年由阿茲特克人(Aztecs)建立,1526 年西班牙人入侵之後一度易名。幾個世紀以來,雖經歷過地震的破壞,至今仍保留著不少巴洛克建築,還有道地的、色彩繽紛的平房,感覺與梅里達有點相似。
瓦哈卡也是我們在墨國南部的最後一站了,我們逗留了兩天,盡情享受屬於墨國南部小鎮特有的情調。我們逛過市內的步行街,還有一個專賣衣服和手工藝品的市場。我買了一條富有當地特色的褲子,本來想要跟老闆議價,不過我完全不懂討價還價之道,最後還是以原價成交。記憶中,這裡的價錢比梅里達的市集便宜一些。
我們一邊享受,也一邊計劃接下來的行程。我們早有默契,確定下一站就是回到距離只有五個小時車程的首都墨西哥城,然後花四、五天的時間北上,再折返墨城,搭早機南下厄瓜多爾首都基多(Quito)。
最後一段的北上路線,我們想過幾種方案,其中大家最嚮往的,就是要一嚐乘坐穿越銅谷(Copper Canyon)的「太平洋鐵路」(Pacifico Railroad)的滋味。要搭這一列火車還真不容易,她的東面起點在墨城西北 1440 公里的 Chihuahua City。搭飛機是最方便的途徑,但價錢太貴;如果要坐巴士,車程起碼要24小時,又太累了。結果我們覺得最折衷的方法,就是租車子,兩個人輪流開車去。
下午時份,我們懷著期待的心情回到墨城,回到那個我們都感到很親切的廣場。結果卻是人面全非。偌大的國旗仍然在廣場中央隨風飄揚,但國旗下閒逸的氣氛消失了,我們看到大批示威民眾在廣場上密密麻麻地搭起了帳篷,標語海報掛在顯眼的地方。我看不懂西文,只看到很多標語上都畫上國際通用的「$」錢的符號,後來聽飯店職員說,是老師們為了爭取加薪而示威。
當時是一九九年六月一日,我想起十年前,同樣的日子,在北京天安門,也有類似的場面。十年前那一場學生運動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十年後看到這樣的場景,又觸動了我心裡面那一根細微的神經。所不同的是,我對眼前那一批示威群眾完全產生不出同理心,我只是一個旅人,一個過客,我還是收拾心情準備北上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