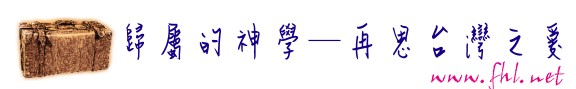 文/葉仁昌
「歸屬與認同」當然不是現在才有的獨特呼聲。但是,台灣當前的「歸屬與認同」的問題,卻面臨了意識形態化的誘惑。不可否認的,台灣的主體意識已經漸漸覺醒了。然而,它卻經常夾雜著歷史仇恨,並且以濃厚的「反抗情愫」(anti-feeling)來看待國民黨此一外來政權及其一切相關的符號象徵,從國號、 國旗、國歌、到國語(北京話)。而在台灣政治的反對勢力中,一種意識形態(ideological )的取向,也逐漸驅逐了原本即相當薄弱的實用主義(pragmatical )政治風格了。 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如果「歸屬與認同」是為了在上帝面前尋索個人與群體的意義,那麼,我們就必需揚棄一種純地域與種族的傲慢自大的態度。因為這種狹窄、自義而沒有愛的「歸屬與認同」,在上帝面前並不能稱「義」。「歸屬與認同」雖然強烈的要求我們以這塊土地為上帝的應許之地,並且在一己的身份上肯定為「台灣之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斷然拒絕在違逆上帝的大愛與義的原則下自私的選擇「鄰舍」與「家園」。
事實上,「歸屬與認同」的真正對象就只是「現時此地」(here & now)。在這個界定下,所謂的「創作模式」的本色化,亦即是「現時此地」化了。我們必需特別提醒的是,「現時此地」的確認不是僵硬的。它乃是經由地理、歷史、血統與上帝的呼召等種種的因素,所交融和激盪而得到的「歸屬與認同」。
同樣的,強調「此地」也不就必然的陷入地域主義。因為「現時」我們雖然踏在「此地」,但或許「未來」由於地理、歷史、血統或上帝呼召等種種因素的變遷,反而使我們從「此地」走到了「彼處」。結果,「過去」的那個「彼處」反而變成了「現時」的「此地」。由此可見,「此地」與「彼處」並不是一種永遠而絕對的區分。尤其在世界已逐漸形成一個所謂的「地球村」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應該有著更開放的心靈來接受「此地」與「彼處」的變遷。事實上,衡諸中國的近代史,許多外省籍同胞的錯誤,就是遷台已數十年之久了,而仍不肯將「過去」的「彼處」認同為「現時」的「此地」。相反的,許多本省籍的同胞則又不肯承認,或許「現時」的「彼處」有朝一日會因為日漸的交流與溝通而成為我們「未來」的「此地」。 這樣看來,「歸屬與認同」是有其動態而富於彈性的一面了。它既不能在屬於時間系列的縱剖面上飄零失根,也不容在屬於空間系列的橫剖面上自我隔離。一方面,它既有環環相扣的「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另一方面,它也有層層相疊的「環境脈絡」(environment context)。而就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發現到原來「本色化」、「現代化」與「世界化」竟是如此的弔詭而不可分割的。
從比較學究的角度來考察,使用「現時此地」這樣一個概念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 第一、它既涵蓋了差異的區域空間,也包括了不同的時間序列。至於「中國」或「台灣」卻純然只是地理上的名詞。事實上,愛因斯坦所提出的「四度空間」說也早已告訴了我們,空間是不存在的,除非時間同時存在。同樣地,我們的區域空間觀念也得接受時間序列的挑戰和變遷;並經由這樣的變遷來歸屬與認同「現時」中的「鄰舍」與「家園」。因此,從「現時此地」出發而為本色神學的進路,實在較之所謂的「中國化」或「台灣化」更為「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第二、「現時此地」這樣的概念也是比較中立與超然的。相反的,所謂的「中國」或「台灣」則包含了強烈的情緒、歷史的包袱與傳統的情結。而這些強烈的情緒、歷史的包袱與傳統的情結,則往往驅使我們陷入意識形態化的危機。「歸屬與認同」的問題誠然在台灣有著「過或不及」的兩極困境。然而,筆者始終堅持相信,我們先是上帝的兒女,然後才是人子。而我們也先是人子,然後才是一個中國或台灣之子。更重要的是,我們愛台灣人,並不是因為「台灣」;而我們愛中國人,也不是因為「中國」。唯一的原因只因為他們是上帝所創造的「人」。 這樣的立場讓我們規避了一種將「中國」或「台灣」當作意識形態來承擔的罪惡。但卻不是讓我們逃避一種把它們當作家園與鄰舍來承擔的職責。其實我們所強調的,只是給鄉土和同胞一種屬乎「神性」的愛。它當然不是只有理性而無激情,它只是拒絕意識形態化。「歸屬與認同」應當出於神性與良知的召喚,並從這樣的召喚中抗拒醜陋的意識形態。它要的是十字架,也因此它厭惡意識形態。然而,今天某些宣講「鄉土神學」的人士卻刻意的將「歸屬與認同」的問題意識形態化。譬如王憲治牧師就鼓吹政治意識形態的建立,因為「沒有神學沒有意識形態的成分;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神學的成分。」這實在是一段荒唐話。神學與意識形態的結合,乃是一個現實性的悲劇。但我們不能以為「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他並沒有體認到,其實意識形態與屬乎上帝的良知是如何的誓不兩立。因為,意識形態強調自己所屬種族、地域或文化的優越性;而十字架卻是虛己和謙卑。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譬喻,意識形態的本質是「肉身」要高舉成為「道」。而十字架的精神卻是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祂「自我約限」在小小的木頭上,並取了奴僕的樣式,「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腓立比書〉二章六至八節)
從基督徒信仰的立場來說,我們不是因為「中國」而背負了中國的一切;也不是因為「台灣」而背負了台灣的一切。我們乃是因為基督。我們因而只有一個十字架,就是基督。民國初期的基督徒,曾經背著國家主義的十字架,現時又要背著「歸屬與認同」的十字架。然而,正確的來說,卻只有基督才是「原生的十字架」(original Cross)。其餘的種族、血統、膚色、黨派、省籍或是國家,則都只是「衍生的十字架」(derived cross)了。事實上,如果不是因著基督,我們根本沒有權利背負任何衍生的十字架。而也因著基督,這些衍生的十字架才不重。 |

索引頁
![]()
版權所有
 歸屬與認同:意識形態化的誘惑
歸屬與認同:意識形態化的誘惑
 更重要的是,強調「現時」並非因而喪失了歷史。因為「現時」必然包含著完整的「過去」,也同時指向了「未來」。同樣的,外省籍的同胞與國民黨也已經在台灣四十多年了。他們都已經成為「現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台灣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道路上,也扮演著不容否定的角色與貢獻。這其中有個道理其實是很淺顯的。「今日之我」在本質上乃是過去歲月的總累績。抽離掉了任何一個「昨日之我」,就將不再是「今日之我」,而是另外一個陌生的存在了。割捨歷史無可避免的是一種嚴重的自戕。它只有在極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為之。以此而言,「歸屬與認同」的真諦,乃是以著前瞻性的態度、富於創造的活在「現時」了。它一方面將「過去」放在「現時」來珍愛與反省;另一方面,則從「現時」指向「未來」而變革與開創。
更重要的是,強調「現時」並非因而喪失了歷史。因為「現時」必然包含著完整的「過去」,也同時指向了「未來」。同樣的,外省籍的同胞與國民黨也已經在台灣四十多年了。他們都已經成為「現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台灣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道路上,也扮演著不容否定的角色與貢獻。這其中有個道理其實是很淺顯的。「今日之我」在本質上乃是過去歲月的總累績。抽離掉了任何一個「昨日之我」,就將不再是「今日之我」,而是另外一個陌生的存在了。割捨歷史無可避免的是一種嚴重的自戕。它只有在極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為之。以此而言,「歸屬與認同」的真諦,乃是以著前瞻性的態度、富於創造的活在「現時」了。它一方面將「過去」放在「現時」來珍愛與反省;另一方面,則從「現時」指向「未來」而變革與開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