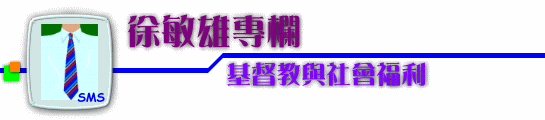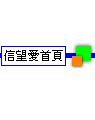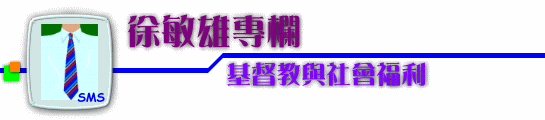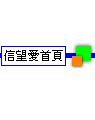從滿清末年到日據時期,一方面是基於當時臺灣社會環境中人民的需要,在西方傳統神學的影響下,
長老教會主要的社會服務的內容以醫療和教育事工為主。但是從日據時代開始,隨著信徒人數和教會數量
的增加,長老教會逐漸發展出層級的代議制度,再加上本土信徒擔任神職人員的比例漸高,甚至進入主要
的領導核心,因此,整個教會在日據時代可以說處於本地信徒和西洋宣教士的轉換過程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對外宣戰,截斷了宣教母國對台灣長老教會一切的人力物力支援後,台灣長
老教會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半推半就地進入自治、自養和自傳的階段。整體來看,日據時代的結束等於是
台灣長老教會領導和經濟自主的分界線,但主要的社會服務事工則仍集中在醫療和教育,因此,本文第一
節的部份乃將一九四四年以前的台灣長老教會劃歸同一個社會服務分期進行討論。
但由於滿清末年和日據時代中教會體制和組織仍然有相當的變遷與改變,所以本文在討論醫療與教育
傳道的社會服務時期時又將其細分為滿清時期和日據時代兩個階段。
 一、滿清末年台灣長老教會的社會服務(約1865-1894年) 一、滿清末年台灣長老教會的社會服務(約1865-1894年)
清朝末年的台灣地處邊疆,當時主要的生存方式以農業為主,不但生活貧困、人口流動率高、疾病流
行,而且族群間的械鬥頻仍,整體來看當時台灣民眾的生活環境很差(Greenhalgh,1994:96)。
在此同時歐洲的海外宣教工作達到了高峰,一八六五年英國籍宣教士馬雅各等人抵達台灣並開始他們
的宣教工作,隨後馬偕等人也於一八七二年在淡水登陸,從此長老教會便在台灣南北兩端各自發展開來。
在文化差異極大,生活環境困苦的情況下,西方的宣教士的信仰理念是有助於基督教的根植?宣教士們要
以何種組織型態這塊土地上開始他們宣教工作呢?
(一)社會環境與醫療事工
當十九世紀末基督教進入台灣的同時,外國軍事干預、經濟侵略和不平等條約可說是同時進行著,一
般人民很少將兩者加以區分,再加上中西文化與價值觀的差異性甚大,所以宣教初期台灣人民對基督教多
抱持著敵視的態度,甚至發生許多迫害宣教士和焚毀教堂的事件。
為了消除台灣人民對基督教和宣教士的偏見與反感,打從一開始宣教士便以「醫療傳道」的方式進行
宣教工作(賴英澤,1995a:24-25;陳南州,1991:70-73)。因為醫療服務對台灣人民來說是很實際的,
不但看得到也感受得到;在人民前往醫療院所接受診治過程中,也增加了民眾和信仰接觸的機會。
從醫療服務中強調福音的傳遞來看,當時的「醫療」不但要減除肉體的疼痛,更強調認識真神的重要
性,宣教士們希望台灣的人民能夠脫離對惡鬼的恐懼,並認識上帝以獲得赦免和救贖。
(二)教會體制、領導模式與教育事工
鑑於台灣的氣候與環境不適合歐洲宣教士長期居住,同時也是對宣教工作本地化的期待,當宣教師抵
達台灣後便很重視本地傳教人才的培養,因此,南北教會皆設立了不少學校,在課程的安排上也以信仰或
教會服事的相關課程為主要內容。
賴英澤(1995:64-67)指出,當時教會中學的設立一方面是作為青年人進入神學校的準備之用,另一
方面也要造就更多好的小學教師,以提高地方教會小學的水準,至於女學校的成立則是為了培育教會內的
婦女,使他們有能力從事宣教和服務工作為主要目的。簡言之,這些教育事工主要都是為了教會宣教事工
開展而興辦的。
雖然教會開辦了諸多的教育事工,但由於台灣民眾的傳統信仰和文化價值已經是根深蒂固,因此本地
信徒對基督信仰的了解僅止於「道德式的」認知,對西方基督教神學中的上帝並沒有確切的了解。相對而
言,無論在信仰或知識水準上西方宣教士都顯示出其獨特之處,在教會的信仰生活中信徒們便有可能對宣
教士們產生一種信服甚至依賴的心態。
因此,從一八七七年南部教會成立開始,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教會主要的事務都是由教士會決定,
包括教師的任免、譴責、待遇及調任,以及教會內的一般事務、醫療館和學校的管理等(賴英澤,1995a:68-71)。
至於北部教會的情況,自一八七二年馬偕進入淡水後的二十年,北部教會的宣教以及諸多事工幾乎完全是
他靠一人負責(張雅玲, 1990;陳玉梅,1995),如果將此一時期南北教會的體制與領導做個比較,雖然
兩教會都是宣教師主導,但不同之處在於馬偕的領導模式近似於 Weber 所謂的「卡理司瑪型權威」
(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1,而南部教會的領導體制則比較傾向一種菁英領導的模式,換言之,此
時期的長老教會無論是在福音或社會服務的事工上,皆由少數外國宣教師負責籌畫與提供。
(三)社會服務與基督教倫理
如果從基督教倫理的角度來看,這群宣教師們在傳統清教「天職」倫理概念的影響下將個人視為「上
帝的工具」,他們產生了熱心的社會服務組織卻不以物質幸福為目的,他們不停歇的勞動,對感官生活也
不斷的加以管束,但這些都不是以勞動生產為最後目的,唯一的目的只在於榮耀上帝,並達到那在揀選中
被認為的拯救(Troeltsch,1960:384-385)。
雖然如此,不可否認地這群清教徒多數都懷抱著相當的人群關懷熱誠,特別是積極入世的服務精神,
對當時衛生環境與知識水準極差的台灣而言,宣教士們適時的醫療與教育服務確實滿足了當時台灣人民的
基本需要。即使當時多數的社會服務只是傳遞福音的管道而非基於任何社會服務的理念,但在服務的過程
中,宣教士依然展現信仰中「愛人如己」的基督教倫理精神。
(四)教會的財務
無論南北教會,宣教師都不斷地鼓勵信徒們建立「自養」的精神,但限於當時台灣人民經濟生活的匱
乏,再加上長老教會初期的信徒以下層民眾為主,因此實際上各項事工的經費來源仍然以仰賴宣教母國支
柱和外籍人士捐款為主,本地信徒的奉獻相當有限。
 註釋 註釋 |
- 對個人及他所啟示或制訂的道德規範或社會秩序之超凡、神聖性、英雄氣概或非凡特質的獻身與效忠(Weber,1996)
|
 二、日據時代長老教會的社會服務(約 1895-1944 年) 二、日據時代長老教會的社會服務(約 1895-1944 年)
(一)本土化神學的開端
日據時代到台灣光復前,長老教會的宣教工作已進行了一段時間,雖然教會和信徒在數量上日益增加
,但神學思想卻仍然停留在西方傳統神學上,而尚未與本地人民生活的實況相結合,因此一切福音事工的
焦點仍然集中在傳遞西方基督教神學與價值觀2(廖安惠,1998)。
但是與前一個時期所不同的是,此時教會在宣教的「方式」上,已經開始注意到本地文化與西方基督
教文化的差異性。為了克服台灣傳統民間信仰的功利價值和信仰道德(或美德)化的情況,長老教會開始
正視台灣本土文化與宣教工作在「方式上」的關聯性(賴英澤,1995a),並從許多方面進行「本土化」3
的工作,以期使基督教的理念更能為台灣人民所接受。
這些本土化的工作中較為顯著的包括教會建築摻雜傳統廟宇的樣式、神學院教育和主日崇拜皆使用台
灣語等。黃武東(1988:36-39)在他的回憶錄中便曾做這樣的描述:
「我第一次做禮拜的牛桃灣教會,是二弄的平階層,外型和一般民家並無兩樣,建築既非西洋式,亦無尖塔和十字架。不僅在牛桃灣,其他地方....早期建築的禮拜堂,其外觀及內面陳設都接近廟宇。....初期的宣教師為避免台灣人心理上的排斥感,連禮拜堂裡的木柵,都與城隍廟的形狀相同。....以鼓報時也是初代宣教師因地制宜的一大改進。....聖詩以本地歌謠配曲,...」
(二)教會體制與財務的發展
1、教會體制與領導型態的轉變
日據時代南部教會的領導階層中開始出現本地的牧師和長老,在教會體制上也設立了南部的大會、中
會和區會,這不但使西方宣教士主導的菁英領導模式開始轉向有本地信徒的參與,同時也確立了南部教會
三級代議的教會體制。
在北部教會方面,由於繼馬偕之後的領導者吳威廉本身深具民主性格,上任不久後便將宣教士組織成
教士會,並以共同協商的方式推展教會事工,隨後更召開了首屆的台北中會會議,訂定「台北長老教會憲
法」(鄭連明,1995c:146-166)。雖然北部教會後來在加拿大母會教派合併的問題的影響下分裂4,使教
會又回到近似馬偕時期的獨裁領導,但在一些力主民主的長老及宣教師改革下,還是回到民主代議的體制
中(鄭連明,1995c:201-203)。
因此,無論南部或北部教會,此時期皆為教會民主代議體制重要的奠基期。在南北教士會和中會紛紛
成立並且邁向自治後,長久以來南北長老教會分治分立的情況便開始受到重視,為了達到教會合一的理想
,一九四三年南北兩大會的議員共同創立「總會」(徐謙信,1995:264-267),這項舉動等於是為日後長
老教會總會的成立作了前導的開路工作。
2、教會的財務
二十世紀初期多數台灣基督徒的生活仍然處於貧困的狀態,但從一九0七年開始,北部教會依然規定
各地方教會在特定禮拜日必須為宣教事工奉獻。一九一二年中會傳道局開始招募「傳道局贊助員」,鼓勵
本地各教會信徒甘心樂意捐出金錢以輔助弱小教會的傳道薪資,這對一般教會信徒自養意識的覺醒有著相
當的助益。
另外,為了保障退休傳教者及其遺族的經濟生活,北部中會於一九0九年設立了「孤寡會」,之後又
與「傳教師養老會」合併為「傳教師孤寡養老會」,該會的成立意味著本地教會開始自己負起傳教師生活
保障的任務。除了這些奉獻外,自養精神也表現在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財團法人的創設上,一九一三年
中會決議將財團法人的名稱訂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中會財團法人5」,財團法人的目的
乃為傳教設置禮拜堂及其他慈善機關之用(鄭連明1995b:151-152),從此,不但北部教會的財產開始有
了正式的規範,本地信徒也在自養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三)社會服務組織的擴大與分工化
隨時代變遷的需要,加上日本政府此時期各項新建設的刺激,此時長老教會的牧師和信徒覺得過去教
會的教育和醫療事工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環境,教會開始有計畫地設立新學校來推展教育事工,並設立了女
學校和婦學堂,其目的仍然是為了培育宣道人員,以應付新時代的傳道工作。此外,為了奠定學校永續發
展的基礎,長老教會於所屬各級學校皆成立了董事會負責管理經營,並聘任具備專業學科學位的基督徒擔
任校長的職務。
在醫療事工方面,在考量民眾就醫便利以及政府的期待下,教會繼續開設新的醫療院所,同時也擴增
了許多新式的醫療設備(郭和烈,1995b:98-99;鄭連明,1995c:193-212;楊士養,1995b:168-192)。
以一八九五到一九二七年彰化基督教醫院的發展來看,教會不但對醫療傳道事工上十分重視,在醫療事工
上也力求服務品質的提昇(楊士養,1995b:173-176)。由此來看,長老教會的醫療事工不再僅是福音工
作的附屬,而是教會事工的發展重點之一,此時的醫療與福音事工可說更加朝向分殊化與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四)日本壓迫下台灣長老教會的轉變
在教勢尚未穩固,台灣本土信徒對於基督教了解不深的情況下,此時期教會關注的焦點自然以福音傳
揚為主。當政權從滿清轉移到日本人手中時,因為初期日本對於基督教的態度較為友善,教會普遍認為日
本人的統治將優於滿清國的官僚體制。
因此,宣教士對於日本的殖民政策是相當寬容,無論是原住民反抗事件(例如霧社事件)或一九一五
年以前漢人的「民變」(如西來庵事件)等,台灣的宣教士似乎不曾對處理事件過程中日軍不人道的殘暴
手段做出反應。雖然日據時代初期曾有宣教士對日本政府對台灣民眾的苛刻提出批評,但不到十年的時間
,教會又轉向給予日本政府相當高的評價(鄭仰恩,1997)。
一九三一年起日本正式對外宣戰,在與西方各國家惡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不但將外籍宣教士強制驅離
台灣,並要求長老教會必須對該國政府若干措施加以「配合」,這些要求不但對當時的教會造成極大的壓
力,宣教母國人力物力資源的斷絕,更使得長久以來仰賴外援的長老教會面臨危急存亡的重大考驗。
在日本強勢的策略下,長老教會部份的教育和醫療機構受到日本政府的干涉,有的甚至遭到強制接管
的命運。外籍宣教士的離台,對台灣長老教會雖然造成不小的衝擊,但也因為這群宣教士的離開,使得過
去一直由外籍宣教士所扮演決策和領導角色空缺了出來,台灣本地的牧師與傳教師開始有機會進入這些高
層位置,教會的菁英遂以本地的信徒為主。另外,也因為外援的斷絕,長老教會必須自行負擔起教會和機
構運作的經費。簡言之,日軍的強制手段雖然對教會產生了傷害,但也是在這樣的危機中,長老教會更快
地邁向自治、自養與自傳的目標。
 註釋 註釋 |
- 這裡所謂的西方基督教神學是基於西方文化與歷史背景所發展出來的神學思潮,我們可以說傳統西方神學是西方世界的「本土神學」,但這種傳統神學常常伴隨著強勢的文化移植,因而對非西方文化造成不少傷害。另外,西方傳統神學由於深受希臘哲學的影響,強調理性、概念以及本質的思辯,這使得傳統神學被人們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抽離出來,進而鑽入學術研究的象牙塔中無法反映出苦難中人們的體驗與盼望,這也是西方傳統神學與本土神學最大的不同點(黃伯和,1995b:9)。
- 一般說來基督宗教的「本土化」發展可能有以下四個方向:1.有形的本土化:包括教堂建築、服裝及詩歌等之民俗化;2.思想的根值:試圖以當地固有的傳統思想來辨明基督教教義;3.社會政治的關懷和參與,以行動表明對不當社會秩序或邪惡勢力的抗爭;4.神學(或福音)的本土化(林本炫,1990:84)。
- 一九二五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因為教派聯合的問題,使母國的長老教會分裂為贊成合併的「聯合教會」和不贊成聯合而維持現狀的「長老教會」。在劃定宣教區時台北教區被歸屬於「長老教會」,因此一九二七年起,加拿大長老教會便承擔起管理北部教區的責任,在商議是否合併的過程中,只有偕叡廉夫婦等少數人不贊成聯合,意見紛歧的狀況下贊成聯合的宣教師輾轉遷移到南部(鄭連明,1995c:201;郭和烈,1995:133)。在這陣大搬風後北部只剩下五位老宣教師,宣教師的離去使教會工作停頓差不多十年之久。正當教會領導陷於真空狀態時,萬華教會的陳清義牧師(也是偕叡廉的姊夫)和偕叡廉兩人便成為教會領導的中心,這使得二十世紀以來由吳威廉和教士會所推展出的民主體制再度恢復到一位宣教師和本地牧師獨自統治教會的局面(鄭連明,1995c:202-203)。這個局面一直到維持到一九三0年左右,受到教會一批留學生所發起的新人運動的衝擊後才得以改善(徐謙信,1995:254-256)。
- 原來北部台灣的各教會自建立後財產都是以個人或「耶穌聖教」的名義登記管理,這樣可能產生許多問題,特別是以個人名義登記者若其子孫的信仰有所改變,教會的財產便會捲入糾紛中。另一方面,這些產業是北部教會的財產,自然也不能歸屬於教士會,因此成立財團法人是最好的處理方式(鄭連明1995b:152;陳宏文譯,1997:91)。
|
 三、醫療、教育服務時期社會服務的綜合分析 三、醫療、教育服務時期社會服務的綜合分析
在清教徒宣教使命的驅策下,馬雅各和馬偕等人開始以醫療的方式傳遞福音的信息,西方宣教士之
所以能夠以醫療的方式達到宣教的目的,台灣落後的醫療環境提供宣教士們一個相當重要的發展空間。
此外,在知識水準低落的情況下,宣教士們勢必要興辦各式教育機構來培育本地的宣教人才。在經
費方面,由於清朝末期台灣民眾生活普遍困苦,所以一切宣教和社會服務所需的費用多數皆由英、加兩
國的差會負擔,或由熱心的基督徒與團體捐款而來。在優勢的醫療服務和知識水準下,再加上外來不斷
的資源提供,宣教士們以醫療服務逐漸獲得民眾的信任,並透過教育事工培育不少本地的信徒,這樣的
社會環境和宣教策略使得滿清末年的長老教會得以順利地在臺灣進行他們的福音工作。
到了日據時代,許多民眾逐漸接受基督信仰甚至受洗成為信徒的同時,教會組織逐漸擴大,在西方
宣教士和本地信徒的推動下,教會體制也日趨健全。至於醫療和教育機構方面,隨著民眾需要的增加,
再加上英、加兩國差會的專業人才和經費補助陸續底台,長老教會醫療和教育機構也朝向組織化和專業
化的方向邁進。
但是,由於教勢尚未穩固,當時的信仰倫理中並沒有公義和人權等概念,因此在日本皇民化教育的
政策下,長老教會各服務機構和地方教會都受到相當壓迫與管制,部份教育機構甚至遭受到強制接管的
命運。
此外,由於當時長老教會尚依賴宣教母國在人力和經費方面的援助,當日本因對外宣戰而強迫教會
與英美差會斷絕關係時,長老教會自然面臨到自治、自養和自傳的挑戰。在這個危急的時刻,長老教會
的教勢不但沒有因而消退,國外資源的斷絕反而促進了本地信徒發展出自治教會體制,在教會經費上也
邁向信徒自足的境界,換言之,這個「移交」的過程是台灣長老教會自主的關鍵所在。
日據時代的社會服務無論是教育或醫療事工都逐漸入朝向專業化的方向,不但多數醫療或教育人員
都並非基督徒,甚至許多的服務都已非必然地夾帶著福音的傳遞。但是這並不就是意味著教會的社會服
務已經脫離了福音,因為無論在醫療或教育服務的機構中都設有傳遞福音的專責組織編制,在推動服務
的方式上還是具有相當的基督教色彩。就此而言,此時期長老教會的社會服務主要的特色應該是福音工
作和社會服務的專業與分工化,教會並沒有僅單方面強調福音工作而忽略了人民在醫療和教育服務的專
業需求。
|